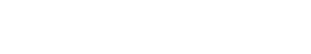邻居
毕华文
几千里外的自治区首府那边,老伴儿给我打来电话。由于时差的关系,老伴儿那里是晚上十二点钟,我们家乡正是半夜。被打扰醒的我有点恼火,正想关机,突然被老伴儿那夹带着哭腔的诉说给挡住了。她说自己从大腿根儿到腰部,起满了红红的疙瘩,又痒又疼,跟负责小区封控的林晓斐提出去医院看病,正值夜班的林晓斐竟说:先等一会儿吧,现在小区有个年纪大的老人出现中风,唯一的一辆公务车送他去医院了,加上人手少,实在顾不上她,请她原谅,让她再等等。
奶奶的!老伴儿在电话里狠狠地说:假模假式的样子!平时看起来挺有范儿的,挺淑女的,挺亲民的!到了关键时刻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看我不到社区告她!我一听这话正想拦阻她,叫她别冲动,不然,好容易建立起来的邻居关系就完了。但我的话还未出唇,电话里就传来了“嘟嘟儿”的忙音——老婆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渐渐熄灭变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再也没有了睡意。老伴儿性格刚强,说过要干的事儿那是一定会干的。
这下好了,刚结识不久的邻居又要成为陌路了!
我们和邻居都住在一楼,门对门。别人都说城市的邻里关系是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可我家和邻居却熟得彼此知道对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差祖坟埋在哪里这点儿不知道了——因为实在没必要知道。
我们相处得这么好,多亏了两家的孩子。
我们家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工作,孙子由我们两个老家伙带着。小家伙虎头虎脑,走到哪儿都有人夸、疼,真的是人见人爱,我和老伴儿也视若心肝;邻居家是个小丫头,瘦瘦的弱弱的,动辄眯着一双长长的睫毛眼睛哭天抹泪,颇有林黛玉那娇羞自我的范儿。丫头比我家孙子大半岁,稍稍懂事一点儿。
一天晚饭后,我们领着孙子在门前的草坪上乘凉,突然,一个叫人喜爱的、洋洋气气的小丫头,手里捏着一块山楂片,“唧唧(弟弟)唧唧”地喊叫着,朝着我家孙子跑过来。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孙子竟头次不认生,接过了那小丫头递给他的东西吃起来。我和老伴儿朝着小丫头跑来的方向看去,见一个年轻的妈妈站在不远处,冲着我们颔首微笑。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而且那么近,门对门。
我们的家属楼是职工住宅,我们又是在这个企业里退休的,对小区住户熟悉得就像熟悉自己脸上的褶皱。对面的老杨两口子不久前搬到汇展园儿子那里去住了,刚贴出房屋出租的信息,马上就有人——喏,就是眼前的这对母女她们家——租下了。
很快,我就了解到:小女孩儿叫如意,妈妈叫林晓斐,爸爸叫王辰。一家三口来自下面一个地州市。两年前,在州上一家单位上班的王辰,辞掉工作,来到首府开了一家烟酒门市部,生意兴隆。开了一段时间后,林晓斐也辞掉原来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工作,带着女儿来到了首府。他们家的店铺在我们小区的附近,一见到贴在小区门口的出租信息,就租下住了进来。林晓斐大学毕业,人也漂亮,气质也好,在我们社区一投简历,就被录用了。没几天,竟当上了我们社区第三网格——也就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党支部书记。
原来,早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林晓斐就入了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突然间,“咣”地一声,新冠疫情来了。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封控措施,王辰的店铺和市面上所有的店铺一样,关张歇业了。王辰年轻力壮的,怎么会闲下来呢,生意做不了了,就干起了志愿者。
因为家中有事儿,疫情爆发之前,我回到老家办理一件棘手的事儿,自然也同样被封在故乡无法回来。虽然两地相隔了几千公里,但党委、政府将民生始终放在第一位,老伴儿和孙子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担忧,因为小区为居民想得很周到,居民除了不能走出房屋随意走动,其余一应生活用品统统替你办好,只要你将需求对志愿者说明,保证准时按需给你送到家门口。
偏偏,大约是被封的第二个星期的第二天夜里,老伴儿就病了。那病——我很快就知道了老伴儿的病情——也很稀罕:红斑狼疮。这种病我还是在看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时听说这个名称的,喜来乐称其为缠腰龙。同时也知道,万一得了这种病,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疼痛不说,治疗起来也很麻烦。原以为这种病挺传奇的,想不到被我老伴儿得上了。
老伴儿的电话打出去没过多大会儿,门铃就被林晓斐揿响了。
老伴儿咬着牙,弯着腰,一瘸一拐打开了房门。
对不起,阿姨!林晓斐一脸惭愧地说,刚才我们领导电话里狠狠地批评了我。是我大意了,想不到你的病这么严重。
跟随林晓斐进来的,还有带着红色志愿者袖标的王辰。
林晓斐搀扶着我老伴儿站稳,对我老伴儿说,公务车一直没有回来,眼下只有让王辰骑自家的电动摩托送你去医院了。边说边流着眼泪道,都是她不好,让阿姨受了苦,自己保证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
老伴儿本来一肚子怨气,虽然给社区领导打的电话上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并没有真正让她消气。现在看到林晓斐这样检讨自己,她再也没有半句怨言,顺顺溜溜地在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下了楼,坐上电动车,在王辰的驾驶下,乘着黄色朦胧的路灯,朝着医院滑去。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小孙子就跟如意在一块玩儿,睡觉和吃饭也都是在林晓斐家。老伴儿吃药,打针,烤电,尤其是打针,每隔八个小时一次,其中一针都是半夜往医院跑,每一次,不是林晓斐,就是王辰,骑着电动车驮着我老伴儿去,直到我老伴儿无需再到医院接受治疗为止。
几个月后从故乡回来,我看老伴儿跟林晓斐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甚至都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才知道这段时间来的担忧纯属多余。
唯一叫人不爽的,是新冠病毒变异的威胁时时存在,从第一代的阿尔法变异病毒,发展到贝塔变异病毒,伽马变异病毒,且不时在全国一些地方爆发。疫情期间,居民的最大要务是定期做核酸,尽管长时间枯燥的防疫生活令人们烦躁,但一想到政府拿出巨额的资金,加上防疫工作者任劳任怨地为大家服务着,所有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出事儿的那天,也是刚刚做完核酸回来,小孙子在我怀里不时地亲吻我的脸颊,跟我打斗,让我高兴得忘记了自己两天来身体的不适。
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常常伏案工作,加班加点,落下了椎间盘突出的病根儿。正是因为这个毛病,我早早地离开了工作单位,赋闲在家。就在头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喝酒时,我迈步子的时候就已经力不从心了,打的回到家就贴了一副膏药,趴在床上烤了半个小时的电,总算缓解了一些。核酸完毕往回走,在单元门口,碰到了对面楼上的工友,也在带孙子。他的孙子骑着一辆滑板车,孙子一见,在我的怀里挣扎着要去骑。我倒换了一下抱姿,端着孩子就往滑板车上放。当腰弯到快九十度的时候,只听我的脊椎“咔吧”一声,登时犹如一股强电流击打了我的全身。我将孙子往地上一放,扶墙挣扎着回到屋子里,就再也动弹不了了。
此刻德尔塔变异病毒正在到处制造传播区域,小区的核酸也由过去的几天一做变为一天一做。我在家中躺着,每天烤电,贴膏药,自然不能来到核酸现场。林晓斐得知我的情况,总是端着核酸的药盘,来到我家亲自为我做核酸。
在床上躺了几天后,以前所有的缓解方法用了个遍,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甚至连翻个身都变得困难起来。我觉得不妙,想到了住院。谁知当救护车来拉我的时候,身子一点都动弹不了了,除了仰面躺着,别人就是稍稍动一下我的身子,都疼得要命。老伴儿没有点子想,第一时间想到了对门的邻居。幸好王辰在家,加上驾驶员,我老伴儿,还有护士,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我用硬板担架抬到救护车里。
在车子发动之前,司机看了看我老伴儿,知道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提醒道:老先生这个情况,是离不开护理的。你们是不是也要提前找个护理?
老伴儿还没接上话,王辰说,反正我的店铺正在装修,闲着也是闲着,就让我去当几天护理吧,阿姨?我老伴儿一看正中下怀,嘴上却说:你一走,晓斐就得一个人带孩子,怕就怕你家林晓斐受累。
没事儿。王辰说,她刚才电话里跟我说了,要我一定照顾好叔叔。
我这人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虽然我打定主意要按照医院的行情给王辰护理费。但我就是不好意思让王辰真的为我端屎端尿,那太难为情了。所以,入院的头三天,除了一两次小便,我一直控制着食量,尽量不让自己解大手。可能王辰把我的事情跟林晓斐说了,第三天的晚上,王辰在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接了一下便交到我的手里,说叔叔,晓斐要跟你通个话。我接过电话,就听林晓斐在那边说,叔叔,你就把王辰当做自家儿子吧,哪有一连好几天不解大手的?这样一来体内的毒素加剧,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的,也不利于病体的康复!
或许是林晓斐的话起了作用,当天夜里,我就开始正常通便了……
至于在医院期间,王辰跑前跑后地忙活,推着我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搀扶我到理疗师推拿,为我治疗转换身体姿势,做我的“拐杖”在大厅里活动……自不必说。在他的照顾下,十天后出院时,我几乎可以生活自理了。
两天后,当我和老伴儿拿着用信封装好的几千块钱,送到对门去的时候,林晓斐和王辰怎么着也不要这个钱。林晓斐说,我是咱们小区的支部书记,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份内的事吗?我老伴儿理直气壮地说:这是给王辰的辛苦费,是他日日夜夜的操劳应得的。
林晓斐说,他是咱们小区的志愿者,伺候叔叔是我给他的任务。王辰也在一旁佐证似的说,的确是这样的,真的没骗您……
这几千块钱到了也没给出去。
可是,近几天一个消息在小区内传播开来:林晓斐和王辰就要搬走了。他们在万达广场买了一套住房,拎包入住的那种。这说明几年里尽管新冠肆虐,王辰的生意还是不错。
当然,像他们这样人品的年轻人,生意不挣钱才怪。
尽管心里多有不舍,我还是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双手合十,虔诚地眯起了饱含热泪的双眼……
聂姐是我所住楼栋的包户干部。平日里,我和她的沟通更多的是通过微信和电话。“亲,天气热,别忘了领取你家宝宝的牛奶。”“亲,你家宝贝今年的医保缴费成功了吗?”“聂姐,给小孩办理身份证,需要在社区办理哪些手续?”“聂姐,节日快乐!”……我和聂姐的互动也频繁,也不频繁。这些年社区干部不易,但凡能自己解决的问题,我一般不会打扰她。第一次见聂姐还是在三年前的秋天,当时,上一任包户干部调去了临近社区,由她接手我住楼栋的包户工作。她于前一天电话联系我,告知我需要完善居民信息,问我是否有时间,她上门登记。我同她约定了见面时间,隔日,也就是周末的早晨,她如约而至。“您好啊,在家吗?我是昨天跟您联系的包户干部聂。”门外传来清脆的敲门声,同时传来的还有一位女士的声音。她的声音很悦耳,听着让人舒适。我当时正在收拾房间,听到声音赶忙停下手中的活计,径直走到房门跟前,按下门把手,快速地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位短发女士,身材矮小,体型偏胖,开门的瞬间,她冲我露出灿烂的微笑,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看到她手里捧着一本很厚的登记簿,封皮是黑色的,也有些陈旧,应该是她昨天电话里提到的居民信息采集卡。我请她进了屋,本想给她倒一杯热奶茶,但她很客气的拒绝了。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户口本,身份证,孩子的出生证等证件,从里屋拿出来递给了她。她接过我手中的证件在桌子上整齐的摊开,再从那本厚厚的登记册中,翻到我家的那一页开始补信息。她的动作有些笨拙,为了掩饰尴尬,她一边抄写一边跟我聊天。我那时小孩不到两岁,正经历女人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的“身心俱疲”,并没有多余的精力闲聊,更何况是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但她全程热情不减,努力的找话题,喋喋不休的说着,她介绍了自己,也很坦诚的表示自己第一次做社区工作,多少有些生疏。很快,她收集好我家的所有信息,起身准备去下一家。临走前,她叮嘱我存好她的联系方式,往后的日子里,若有事可以随时找她,她会尽全力帮助解决。
后来的三年,她是真的兑现了当初的承诺。但凡我电话,微信联系她,她总是及时回应并耐心解答。她清楚的记得我的名字,职业以及我的家人。我面对的是她一个人,而她面对的是几千户的居民。对每一户的信息了如指掌,又能够做到随时随地的对居民“有求必应”,是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事。如此看来,聂姐做到了。我和聂姐线下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直到疫情来袭, 聂姐又多了一个技能,就是给居民采核酸。今年冬天,也是一个周末,我带着女儿去地下车库的指定地点做核酸。排队的过程中,远远看到两位“大白”坐在红色的塑料板凳上,面前的木桌子上放着采样管,棉签,消毒水等物件。她们拆棉签的包装,给居民采样,再放到采样管中点几下,将棉签扔进一旁的医疗垃圾袋中,最后按压消毒液给手消毒……两个人有条不紊地重复以上动作,整个流程很顺畅。
四岁的女儿目不转睛的盯着她们,良久,说了一句:“妈妈,那些‘医生’看起来好辛苦。”穿一身白色防护服的“大白”们在女儿眼里也是白衣天使。“是的,她们很辛苦。”我回答。终于轮到我和女儿,我打开手机截屏图片,工作人员扫了码,示意我们过去采样。因为已经有了先前很多次的经验,四岁的女儿不像更小的时候那样哭了,她很配合地张开嘴巴,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啊……”。“小朋友真乖!”突然,给女儿采样的大白夸赞到。我感觉这声音很熟悉,抬头与她的目光触碰,眼前的这位大白居然是聂姐!严严实实的防护服下,虽然只能看到一双眼睛,但我还是认出了她。“聂姐,是你啊!”我惊讶的看望着她。“哎呀,你认出我了啊!”她回答,语气中略带一丝欣慰。
从前在微信语音和电话一端听到的声音,此刻从防护服的深处传来,虽然传输的过程中被迫加入了一丝被闷住的“特效”,但依然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可爱可敬的包户干部聂姐独有的声音。我赶忙叫女儿向她问好,“阿姨好!”女儿朝她挥着小手。“宝贝的个子又长高了呢!”她转身热情的回应。在那之后的每个周末里,我总能在小区见到聂姐采核酸的身影。冬天她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那里又冷又潮湿,她和同伴周围只有一个小小的电暖炉。开春后,两栋楼之间的小路上,聂姐坐在小板凳上,一直一直地给居民采核酸。夏天,她和同事们坐在遮挡烈日的帐篷下,但望着她们也还是觉得热,终于轮到自己做核酸,与她们四目相对,透过护目镜能清楚的看见堆积在她们眼睛周围的汗水,在一滴一滴的往下流。我从她身旁走过,总会大声地朝她打招呼:“聂姐!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是她一惯的回答。
近几日,我在小区做志愿者,见到聂姐的次数更多了,她依旧是一身“大白”的装扮,忙忙碌碌的身影穿梭在小区角角落落。有时她提着医疗垃袋圾匆匆走过我所在的单元门口,有时她骑着电动车与时间赛跑,从一个楼栋奔向另一个楼栋,给居家的住户上门采核酸。她说自己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记得她有个儿子,也还在上学。她肯定也想家,也想自己的孩子吧。全民共同抗击疫情的道路上,狡猾的病毒反复“变身”,一次次的考验我们的耐心。但总有人保持初心和耐心,一直坚持着做好一件事。他们是平凡岗位上的逆行者,他们的故事不曾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