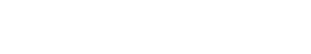作者简介
黎子,1993年生于甘肃庆阳。2014年开始文学创作,有作品发表于《西部》《草原》《作品》《厦门文学》《广西文学》《散文选刊》《扬子江诗刊》等刊。曾获《人民文学》高校征文大赛一等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现居重庆。
清早,窗外的天光蒙蒙亮了。福根起炕,套那条压在炕角的冬裤,婆娘杏芳的腿伸过来,压住冬裤,还去啊?天冷,不去了。
福根把裤腰拾掇齐整,用最外面的一根麻花布绳在腰上勒紧,打个活结,手朝肚子上拍两下,恍惚的尘埃飞起来。他套上棉袄,抬起左腿,下了炕,把压在炕席下那把刀拿出来,别进裤腰里。杏芳醒了,被子蒙着半张脸,露出乱蓬蓬的头发和一双红血丝遍布的棕黄色眼睛。她哆嗦着身子,天冷的,你不怕手起口子?
福根从咽喉里发出一个浑浊的声音。他朝地上吐了口痰,转身蛰进窑掌里,摸黑在水瓮里舀了一马勺清水,端着出了窑门。马勺里的清水左右激荡,摇晃着,摇晃着,终究没有一滴洒出来。
福根家的窑洞院子在半山腰。出了门,上个短坡,往前走十几步路,是个朝山腰上戳出去的山嘴,悬在半空,站上去,可俯瞰整个玛瑙川的山川河流。玛瑙川是黄土高原上一个不大的川子,曾经热闹熙攘过,如今也像别的乡野与山村一样,凋敝零落了。
清晨薄暮层层叠叠升起来,越过山峁的脖颈和白杨树的腰身,落在山嘴上。已是深冬,四野荒草披着散霜薄雪,被朝阳映着,一粒一粒,闪着红彤彤的金光。隆冬的太阳只在早上通红这一会儿,没多久,就会变得煞白,白成一只黯然失神的瞳孔挂在天空硕大的头颅上。福根眯着眼,在短暂的红日下立了一会儿,一颗泪珠从他眼角浸出来。匍匐在山嘴的磨刀石结冰了,像一只全身挂满冰凌动弹不得的暮年虎,它立在旭日下等待太阳的救赎。福根把半马勺冷水泼上那冻僵的老虎背上,水顺着冰凌清脆滑落。这并不碍事儿,不出半根香工夫,福根的刀子会让虎背上的冰和水都冒起腾腾白气来。
整整有半年了,福根每天日出日落来这个山嘴上磨刀。其他时间要上山放羊,下地拾掇庄稼,他还是没忘记干了一辈子的这些营生。他舍不得他的土地。川里人都说,恓惶的福根啊,怕是傻了,天天磨刀,是想给女儿报仇吗?可他一个瘸腿的哑巴,能走到哪儿去呢!
毫无疑问,福根是整个玛瑙川最能干的庄稼人。其他能干的庄稼汉,能出门打工的都出门了,最不济也在河州城的工地上搬砖头、拉沙子,去盖高楼大厦了。地里种不出钱,如今没人种地了。福根的腿不灵便,又咿咿呀呀说不清楚话,他不进城,依旧留在玛瑙川,种他的地,放他的羊。
福根的腿脚跟舌头不灵光,但他的脑子灵光,会做事儿,又肯下功夫。早些年,大家都种地,他放羊,规模最大的时候,他的羊群繁衍到了一百只,关了整整一个地坑院,五孔窑洞。后来大家都弃地从工了,他把羊卖了,只留下十只山羊。清早打开羊圈放到山上去,由领头羊带着,吃完草羊群自己就下山回来了,用不着多操心。他把卖羊的钱,一部分供儿子读大学,一部分承包了川里最肥沃的河畔田地,种了苹果树、柿子树、榛子树,树种都是村委会免费发放的,说是扶持农民创业。还有八亩地,他养了松树苗,这些树苗长到半人高就有城里人下来买,买到城里去做街道绿化。还有十几亩地,他一年四季种着小麦、玉米、高粱、菜籽、胡麻、糜子、小谷。春夏之际还会腾出河滩的两三亩石头地,种些西瓜和梨瓜。一对儿女放暑假回来了,最爱钻到瓜棚里去。瓜棚里有床板和被子,晚上在棚头挂上马灯和蒿子,看守瓜田。儿子女儿钻在瓜棚里,拿个长刀把西瓜劈开,一边啃着西瓜,一边吆喝着吓走那些野兽。
女儿最爱吃一种灯笼红品种的梨瓜。福根记得。那时他叫杏芳去集上买种籽,一定会买上两包灯笼红种籽的。
这年冬至,玛瑙川的人都从河州城里返回村庄拜祖。那些冷落许久的烟囱里冒出炊烟,在玛瑙川上空弯弯曲曲作画。玛瑙河对面的黑水龙王庙,平日里锁着,今天也开门了。庙里供上了香火和花馍馍,红色幡子在屋檐上随风飘摇。人们清早揣着香表去庙上拜龙王,有人从小桥上走路去,有人开汽车从大桥上一溜烟就到了庙门前。男人们烧完香,从里面出来,立在庙门前抽烟。有人感叹,龙王庙破了旧了,大家应该捐点钱,把庙子重新修葺一番,或盖个更大更气派的。有人点头应和,有人摇摇头,唉,修它做啥,有这闲钱,还是攒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吧。人们三三两两谝着闲传,过了河,回村庄了。
晌午,日头朝西偏去,福根家院落里留下半扇日影,轻晃晃移动着,那是日头翕变的翅膀。人们聚在福根家吃饭,打鼓,给已故的先人磕头、放炮、点纸钱。聚在院子的人,手里揣着一部手机,边磕头边拍小视频发朋友圈,配文:祭祖的日子,回家寻根,给我老祖宗磕头了……在城里待久了,人们反而觉出了这乡下的有趣和放松,举着手机各处拍着,攀谈着,一派热闹融融的景象。
玛瑙川人没有祠堂,祖先的牌位和家谱都是三年一家轮着伺候的。今年轮到福根家。福根提前宰了一头猪,这天叫杏芳煮了,一口大铁锅支在院里,柴火热烈燃烧,锅里炖着大块的骨头。铁锅旁临时支起来的案板上,放了一摞瓷碗,锅里戳着一把一米长的铁勺,要喝汤自己走过去舀就成了。杏芳还在窑里忙活,和几个女人和面、切菜,准备吃了猪肉,再让大家吃碗饸饹面。城里的饸饹面不好吃,清汤寡水的,没味儿!那些回乡的男人女人都这么对杏芳说:“还是大伙儿聚一块儿,大锅熬出来的热汤淋上长面,那才叫一个美咧!”杏芳便叫粉娥嫂子去窑洞门口喊一喊。粉娥双手叉腰,立在窑门口朝院里喊:“男人婆娘娃娃们,赶紧把锅里骨头都啃完,老娘等着大铁锅调汤咧,你们还想不想吃饸饹面喽——”
“想吃,想吃得很——不光想吃面,还想喝你的汤咧!”院里一个男人扯嗓子吼了声,大伙儿都跟着笑了。
那只小山羊,就是这时从窑面上跌下来的。跌在半空,挂在一棵椿树杈上。
黄土簌簌落下来,扑了粉娥一脸。女人大叫起来,转身走进窑里,从缸里舀起一瓢水来洗脸。人群齐齐抬起头,惊呼起来,仿佛发现了一个新闻现场似的兴奋,手机摄像头对准身悬半空的小羊。
杏芳跑出窑门,抬头看到悬在崖面的羊羔,吓得大叫福根的名字。福根从祖先的供桌前起身,一摇一晃走出来,看到椿树杈上挣扎的羊羔,腿脚乱蹬着,崖面的土块啪嗒啪嗒往下掉。
福根认出了这只羊。这是今年过端午时长须母羊诞下的一只羊崽,也是母的,如今已长到半大了。
母羊诞羊羔那天,女儿刚好放学回家。女儿在城里念书,高二了,学习时间紧迫,一个月回一次家。她手里捏着书本来到羊圈,看父亲为母羊接生。小羊的头出来了,身子还卡在里面,父亲口齿不清地喊女儿的名字,蓝——蓝——他打手势叫女儿进来帮他一把,把羊腿摁住,这羊难产了。
十七岁的女儿看到这个鲜血淋漓的接生场面似乎被惊吓了,又有些害羞,远远地站在窑门前不愿挪动。她毕竟是农家长大的女娃,懂事、勤劳,踌躇了一下就进来了,把课本放在一旁的羊槽里,弯下腰帮父亲安抚那只可怜的母羊。一炷香时间过去了,母羊顺利诞下羊羔。福根把一盆小米汤端到母羊跟前,母羊艰难地站起身,把头伸进脸盆里喝米汤。不大一会儿,那只小羊颤颤巍巍站起来,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便跪下前腿去母羊身下吃奶。女儿看到这一幕,眼里闪起泪花。爸,羊羔子真坚强,我也会像它一样。
女儿当时说了这么一句。福根欣慰地点点头,那时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会好起来的。
杏芳在院里乱窜,嚷嚷着找木锅盖,要盖到那口大铁锅上。
落进了土,肉汤就喝不成了。她嘴里不停念叨。
福根一瘸一拐穿过人缝儿,在草棚的木梁上找到一根长绳。他把绳子取下来缠在胳膊上,又进厨窑,从炕席下取出那把刀别在腰上。走出院门的时候,他回头望,羊崽还在椿树上蹦跶。母羊在崖顶上朝下呼号,蹬着蹄子,急切地呼唤它的孩子。人群中响起尖叫声,要掉下来了吗?啊,快掉下来了——
福根本想叫个人跟他一起上去的。他环视一圈,发现他的婆娘急着收院里的菜碟碗筷,其他人捧着手机仰头呼喊。他把手放在那把刀上,紧紧攒住,喉咙里发出一个沉闷的咳嗽声,转身,踉跄上了坡。
母羊见福根上来了,奔过来跪在福根身下蹭他的裤腿,一双羊眼里泪汪汪的。福根摸摸母羊的头,似乎在说,放心吧。相比于跟人相处,福根更愿意和牲畜待在一起。动物的灵性和善意常常比人实诚,这一点让福根感激,跟它们在一起时,他不会孤独。
福根将那把三寸长的刀子插进一个长草的小土堆。这样的土,内部有草根勾连,往往比较结实。他把绳子绑到刀把儿上,来回拽动,试探着绳子的牢固程度和承受力。或许是嘶叫得累了,小山羊嗓子已沙哑,它无望地安静下来。
下方院里的吼叫声又惊扰了它。羊娃子,你倒是动一动啊,是死了吗?没死没死,又动弹喽。动弹拍起来好看……
安静下来的羊羔又开始四蹄乱蹬。椿树枝摇摇欲坠,再攒动,就要折断了。福根心里着急,想让底下的人闭嘴,不要再乱吼乱叫了,可他张口,只发出一阵咿咿呀呀浑浊不清的声音。
他张开了嘴却吐不出一个字,声音仿佛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吐出来,就变成了无力的哽咽。他只好拔出那把刀,把它举起来,朝下面的人挥舞,想告诉大家不要吵。他日日打磨的刀子太过明亮,在崖顶上划出了一道炫目的光芒。人群再度响起一阵尖叫,手机镜头朝上,齐齐对准了他。“福根家的羊跌死了,福根拿着刀子,要跳窑面子了!快看啊——”他们这样嚷道。
福根感觉自己的耳朵嗡嗡地响,要裂开了一样。
......
全文请阅《西部》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