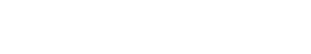作者简介
习习,甘肃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十三届高研班学员。著有散文集《浮现》《表达》《流徙》《风情》《风吹彻》、纪实文学作品集《讲述她们》、历史文化随笔集《公主和亲--那一抹历史深处的胭脂红》、小说报告文学集《翩然而至》、人物传记《区炳文传》等。
远 方
习习
天气很重要吗?
一
去看年迈的父亲,进了院子,见许多人目不转睛仰着头,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没看出异样,问他们怎么了,一个人伸长手指说,那人要跳楼。楼层太高,人小到看不清。楼下排列着升降车、鼓足气的救生垫、救护车……
上电梯到二十六层,一头钻到靠近院子的小屋,隔着场院,小屋的窗户竟正对着那个窗口。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那人保持同一姿势站着,是个年轻男子。我坐在窗前,一动不动面对着他,仿佛对峙。那么窄的窗沿,怎么站得住?天气又那么冷。
外面飘着雪粒子,干燥的没有黏性的雪粒子。虚空肃穆的冬天,悬置在我们之间,鸽群在他面前飞来飞去。再远处,可以看到黄河,有一刻,一架飞机从他头顶飞过。看上去,命悬一线的他,竟静若处子。焦虑的似乎是飘雪、河流、飞鸽,和那架隐入云层的飞机。他当然不知道对面一扇窗户里,有个人看着他,调动五脏六腑因他思虑、为他紧张。四个多小时过了,他还是站着不动。天色已经昏暗,倏然间,他身后的窗户被人打开,他被拦腰抱进屋里。窗沿空了,楼下的人们纷纷散去,救生垫急速瘪了,升降车、救护车迅速开出院子。仿佛一场看似紧张又过于冗长的戏落下了帷幕。他活下来了,这是我猜想的结果之一,而结果无非两个,非生即死或非死即生,生与死,一线之间。我想起先前无意中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人从高楼跳下,带着重力加速度急速下降,快落地时,人已然僵死,人们遽然尖叫,然后一片静默。
面对真实的死亡,思考显得那么单薄。
那日从父亲那里出来,雪粒子迎面打在脸上,天多冷啊。一个人像冰冻了似的悬了那么久,也算死过一回了。这样的“死”,抑或沉降为精神意义上的某种分量,抑或什么都留不下。很多年前,我不大懂,人们写日记时,一开笔,除了记上日期,还要写上天气。后来我明白了一些,日子是可以在密集的时间之网上寻到的坐标,是人为的确定,而天气才是这个坐标上风起云涌、变幻无定的背景。
二
很多刻骨的事,和天气融为一体。
我和姐姐站在楼下,冬至过后的第一天,那年隆冬最冷的一天。我们在楼下的枯树边浑身发抖。喜鹊的叫声很大很尖锐。几个男人敲不开弟弟的门,翻进二楼窗户,说弟弟死了。他们没有形容他的样子,我也坚决不要他们形容。前一晚,弟弟还吃了我们包的冬至的饺子。早上,我在楼道拼命敲门时,已经感到那种从未有过的阴冷、人世上没有的阴冷,从门缝里、锁眼里飘出来。
我们在枯树下,看人们抬下一口棺材,我们浑身颤抖。天在下雪,是雪粒子,干干的雪,地上薄薄的一层白色,跟着风跑。姐姐不时哭号一声,然后戛然而止,我没哭。人们老说心疼心疼,心真的会疼。有人说一起上车吧,送他一程。我们挤在逼仄的车厢里,弟弟在棺材里,我的腿抵着棺材,仿佛抵着他的腿。冰凉啊!几年了,孤单重病的弟弟一直喊冷,窗外进来的再烫的太阳,也晒不热他。弟弟说过,姐,我死了一定把我放在热的地方。
好了,现在终于热了。我们抱着他温热的骨灰,在怀里。我一点儿都不怕了。那天是农历十五,月圆之夜,我们到桥上,到河流最湍急的地方,把他的骨灰撒进河里,骨灰干净温暖,河水长流,最后到海里,暖暖的海水里。我没有流泪,只是回头,又回头,看河的最远处。月亮又大又圆,温暖的橘色,它静悄悄地俯视着河,俯视着河边的我们大悲大痛。
我后来梦见过弟弟一次,他全身缠着白纱带,春暖花开,彩色的梦,弟弟好像不疼,他在痊愈,白净漂亮的脸上全是笑意。我跟姐姐说,弟弟现在不疼了,也不冷了,他现在过得很好。
天气怎么不重要呢?天气是时间伸过来的一根长线,一直伸到你心上,一不小心就扽得你心疼。
三
杭州,西湖边,台风遽然而至。金桂开得正好,风把桂花摇了一地。先是小雨,忽而转为瓢泼大雨。仿佛某个无形的巨怪呼啸着从空中飞奔而来。刚才,西湖断桥上还在搞大型表演,现在,厚重的雨幕里,人影全无。雨太急,挤进一家快餐店,说是历史上一位名人曾经的院落。正对着西湖,尤其是正对着西湖断桥的院落,真是个好院落。雨像在泼,人们纷纷挤进来。我第一次离西湖这么近,干吗蜗居在这里?迎着往里挤的人再挤出去。断桥上,铺满桂花,雨水没有隔断桂花的甜香。大雨里前行,仿佛逆流而上。天与地与山与湖水,一片灰白。
我终于找到冒雨前行的原因了。
天上的云雨翻卷成一条深灰色的长龙,紧压着湖面。我看到湖心岛了,张岱写过的湖心岛。
“崇祯五年十二月,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张岱的大雪中的西湖,是沆沆漭漭的静默。我眼中的西湖,正沆沆砀砀的激烈。张岱在深夜,划船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岛上有两人铺毡对坐,炉上酒水正沸,张岱饮三大白而别,船夫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先时,读这个小品文,每看到张岱写船夫的喃喃自语,就觉得快活,就又回过头看张岱是怎么写湖心亭看雪的。那么短的文章,写进了五个人,还有天、水、山、酒炉、船……雪盛大啊,静悄悄地,把看得见的人、物,看不见的心情都尽数囊括。
我在大雨的西湖边伫立,心里欢快至极。那是我对西湖至深的一次印象,那个西湖就是张岱湖心亭看雪的西湖呀。
西泠印社的门已经关了,雨在路面凿满欢快的水泡。既然湿透了,索性就踏雨而行。来时,我在里面买了一支毛笔、两块紫檀镇纸。我想带一些江南的东西回去,当然还有这个奇异的天气。
四
说话的人讲着我听不懂的粤语,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正接受我的采访。讲的是她年轻时的一件事,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一脸。一个过了大半生的女人,什么事儿让她这样动情?我那天回去后,一边听录音,一边读别人用普通话翻译过来的文字。说那天她用小船运满树苗,到河对面镇上去卖。这船树苗是她在自家地里精心养了三四年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有三个孩子,屋里的家具只一张饭桌。河叫横琴河,对面的镇子叫小榄镇,小榄镇是珠三角有名的苗木集散地。那天,她独自撑船,快到河心时,船被养鱼人家的格网缠住了。正焦急时,天又变了,好像是她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暴雨,船晃得要翻,她疯了似的喊救命,可是叫天天不应,想到亲人,眼泪和雨水一起在脸上淌。忽然对面来了一条小船,船上有人大喊:你不要命了吗?是两个男人,把她拉上他们的船,风雨过后,又帮她解开缠在网上的小船……
我听不懂粤语,但听到了她动情时的声调。她后来用几十年找这两个恩人,没一点儿音讯。她说,一定是老天派来的神仙。我听出了她语调里的深情。
但动笔时,我无法进入那个场景。
西北雨水少,但凡大雨,往往都是酝酿许久、有备而来的。我想起,同样在广东,在一个小镇的电子厂,我待了两周,采访了很多年轻工人。是盛夏,我和一个漂亮女孩住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宿舍。有时,关了灯,我们会聊一些亲近的话题。她问我,好多人说我像电视剧《红楼梦》里的陈晓旭,你说像吗?我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很像陈晓旭,但我思忖片刻说,不像。她又问我,《红楼梦》里你喜欢黛玉还是宝钗,我一点儿不犹豫地说,黛玉。
那天,我坐在工厂院里的铁椅上整理采访笔记,毫无迹象的,大雨突降,雨水把头顶的铁棚子砸得乱响。我没见过这么急脾气的大雨,很快,雨又停了,气温马上升起来了,地上看不到积水,细看厂院里盛开的嫩黄的鸡蛋花,花瓣上竟没一滴雨水。
后来,我去广东茂名。朋友带我去古荔枝园,行进间,天色大变,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车无法前行,只好停在江边,江边的树木在狂风中激烈地俯仰。我在车里,感受着这场持续了几十分钟的大雨,那个女人在横琴河上遇险的一幕,真切地出现在了我眼前。那天,回到住处,我第一时间修改了那部分采访文字。
暴雨刻骨铭心地下在那个女人的心上,就这样,也下在了我的文字里。那天,住在海边,大雨洗过的海滩和海上的黄昏,奇妙得不可思议。我见到了此生没有见过的最瑰丽的晚霞。有人说,大海是不可描述的,大海之上的天空也是不可描述的。我的表达,面对这样的神奇,显得如此窘迫。
三棵树
一
那棵臭椿长在我家小院。小院是工厂家属大院的一个犄角。
上学时,才知道臭椿还有个模样相似的姊妹,叫香椿。臭椿和香椿,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金姬和银姬,一对孪生姐妹,因为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一南一北,命运截然不同。树因为气味迥然,也有了命运的况味。香椿的香主要关乎人类的味觉,是实用主义的香。香椿刚发芽,叶子还稚嫩到无力伸展,很多枝丫就夭折在人们手里,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了。
这样看来,臭椿好像用“臭”保护了自己。
那棵粗大的臭椿立在我家小院中间,在我幼时,陪了我很多年。
它第一时间带来季节的信号,西北灰蒙蒙的长冬过去,到四月末,它洒下一地小米粒的黄绿花,那种浓郁的特别的“臭”味就是小碎花散发出来的,这时房檐上父亲压在大花盆里的白葡萄枝还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漫长的夏秋,臭椿一身浓绿,阳光照过它的枝叶,洒下一地光斑。我和姐姐跳皮筋,老是缺一个人,就让臭椿在那一边抻着。有一年,臭椿要压到屋檐上了,父亲搭着梯子,锯下过于茁壮的枝叶,好让屋子里进来些阳光。冬天,叶子落尽,臭椿枝条上剩的是一簇簇由金红变成枯黄的豆荚,它们簇拥成一团一团,到下一年开春时还结实地挂在树上。包着种子的豆荚,学名叫翅果。豆荚像长了翅膀,可以带着种子到处飞,所以,我家后墙外水沟边的坡地上,歪歪斜斜站着的多是臭椿。翅果落下来的样子很好看,竖着身子,轻飘飘、一扭一扭的。
大风刮起来,臭椿枝条翻飞,带着风给的力气,看起来有些可怕。父母在工厂上夜班,风雨天的夜晚我不敢独自回家,大院的孩子说,你家院里树上住着鬼,绿头发绿牙齿,大风一刮就把它刮醒了。远远望去,它的粗枝大叶,乖张地上下俯仰,哪里有一点儿平日的文静。
人总是陪不过树,后来小院里的屋子,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雨中,后墙坍塌。我们被迫搬到了别处。
此后,那个臭椿下的小院和小院里的家,常进到我的梦里,给我们喝羊奶的母羊还是拴在树上,端午节前一天母亲下了夜班做的一大盆红枣糯米年糕还是晾在树下。
其实那棵臭椿不一定很茁壮高大,只是因为我年幼。就说我在上小学时,下课时,我一溜烟儿从二楼扶梯滑到一楼,伸开两只胳膊,感觉像鸟儿一样轻快地飞了好久。多年后,我路过小学,进去一看,楼房低矮得像佝偻的老人,扶梯短促到根本没法滑行。
一棵和你生活久了的树,怎么能把它忘掉?你想在纸上画出记忆中那个简陋的家,那个伸着屋檐的土坯屋子,玻璃窗户大睁着眼睛。画纸上,树一定站在屋外,枝叶挠着窗户。如果坐在屋里的炕上,抬眼到窗外,第一眼看到的还是那棵树。冬天,它像睡着了,很安静,但稍大些的风吹过,那些簇拥的豆荚就发出干燥的推搡声——沙沙沙——今天还能听见。
二
另一棵树,还是臭椿,长在大院里。大院畅快,没有拘囿,那棵臭椿应该比我家小院那棵蓬勃高大很多。到现在我还记得围着这棵树排列过去的各家各户:兰兰家、玲玲家、莲娃家、菊梅家、大红小红家、长生家……那时,不知为何,大人们在树干上绑了一根长长的铁棍,我们攀着铁棍蹿上蹿下,把它蹭得滑亮,慢慢地,它几乎长成了树的一部分。晚饭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蹿铁棍。两手紧抓铁棍,双脚抵着树,几乎横躺着,飞快地蹿到树杈上,很多孩子也喜欢蹿铁棍,但都没我快。我热爱那种感觉,那一刻,我仿佛一个实实在在能够上天入地的女英雄,没了日常的羞怯。其实,那是蛰伏的另一个我。
臭椿在大院洒下一地绿碎花时,树下面像铺了一张毛茸茸的毯子。大人们嫌烦它,咯吱咯吱,踩坏它们也不心疼。过于静美的东西,我总舍不得破坏。就像大雪后的清晨,一地厚墩墩新鲜的白雪,怎么都不知道把第一脚伸到哪里。所以,如果你听说,有人还没踩到雪,就好端端地被雪绊倒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臭椿的学名叫“樗”。我很爱这个字,看见这个字,就立刻觉出了它挺拔入云的样子。
三
还有一棵树,也在时间的远处,叫秋子树。它长在与大院一墙之隔的木器厂的两排车间中间。
秋子树结的果子叫“秋子”,不成熟的秋子淡绿色,味道极为尖酸,在滋味匮乏的时代,这种极端的味道很解馋。秋子长到刚刚能入嘴的时候,我们疯了似的想尽办法混进工厂。那棵果实丰饶的秋子树,就那么玉树临风地站在人字形顶棚的车间旁边。它很高,怎么摘到秋子呢?须得上到车间房顶,从低一点的房顶爬到高一点的,直到能摘到秋子。口袋一定不够装,就直接从领口塞进衣服,或者脱下外衣,扎住袖口,把秋子装进两只袖子。收获满满,一身鼓鼓囊囊,混迹在下班的工人里,出厂门回家,把秋子倾倒在炕上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成熟的秋子是什么颜色?金红金红,树像顶着一片火烧云。深秋,树尖上那些金红的秋子就那样烦人地高高挂着。你想发脾气,往树身上狠狠踢几脚,疼的是你,树和那些金红的小果子纹丝不动。
秋子树多么美好啊,只是,在我们城市里我再没发现过第二棵,说到秋子果时也无人知晓。木器厂后来渐渐消匿在城市的楼群里了。很多时候,我以为我早忘了那棵秋子树,就在去年盛夏,我在公交车上,路过先前的木器厂时,在一片新开的工地旁,突然看到了那棵满身浓绿的秋子树,眼睛猝不及防地湿了。
原来秋子树还在啊,在这个人潮拥挤的世上,我多么感激让它活下来的人们。
小鸟的脖子酸了
一
我们几个人到达河西走廊民勤县内巴丹吉林沙漠边上的那个村子时,天已经黑透了。白天,我们探访了藏在戈壁深处的沙井子史前文化和戈壁滩上相呼应的连古城遗址和三角城遗址。车停在村委会一棵大树下时,一树夜宿的鸟儿扑棱棱飞了起来,一抬头,满天星斗。我们要借宿在一户村民家,驻村干部说男主人到沙漠放羊去了,问他,村子远吗?他手指一伸说,对面,二十几米。我们跟着他走,天硬生生地冷啊,村干部一只手高高撑着一纸盒鸡蛋,闲庭信步似的。太冷了,好像走不到头的样子,这哪里是二十米。村干部穿着单薄的西服,腰杆笔直,那盒鸡蛋在他手掌上始终撑得平平的。
门帘掀开,热气轰然扑来,烤箱的火烧得很旺,女主人一一打量过我们后,开始铺炕。炉子和炕连着。收拾停当,女主人退出门说去另一间屋睡。
我舍不得那一天的星斗,很多年前,我在嘉峪关外的戈壁上看过这样的星斗,又大又亮又密,远处的星斗好像落到了地上。屋外的羊圈是看星星的好地方,羊圈里的羊粪有几尺厚,踩到上面,晃晃悠悠。没有月亮,满满一天的星斗在沉寂黝黑里,夺目得让人心颤。
炕太烫,滚来滚去,把半拉被子铺着隔热。四周静得出奇,忽然木门一阵晃动,咚的一声,有东西从天窗跳了进来,吓得一激灵。原来是猫,我们占了它的热炕。
一早到村子转。驻村干部说得不错,隔着水渠,对面就是村委会,二十来米,一抬腿就到,只是绕着村子的水渠正放水。水是从水库引过来的。多年前,我到民勤采访过一对几十年治沙防沙的老人,那时,公路上到处可见“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标语,而今,民勤的自然风貌已大有改观。五月了,枣树叶子还很稚嫩。村子很精巧,一眼能看到不远处的沙漠。那年在武威也看过类似的情景。过了公路,不远的田里,一个老汉带着孙子正挖蔓菁,地那边就是白花花的沙漠。
村子和沙漠,迥异的两样事物就在面前,一个顽劣地保持着广袤和荒凉,一个拗着身边这个大事物的性子,被一代代人改造得完整而富有生机。说起来,这个已经活过十几辈人的村子,硬是和身边的巴丹吉林相安无事。当地人说,“巴丹吉林”四个字讲的是一个叫巴丹的放羊老汉在沙漠上发现了六十多个海子。巴丹老汉会不会就是从这个紧贴着巴丹吉林沙漠的村子出去的呢?
女主人歉疚地说,忘了把猫儿领进她睡的屋子。她麻利地打了一锅荷包蛋,蛋是驻村干部昨晚带来的。女主人舀出一个蛋放在炉子边,猫卧在一边,目不转睛看着它变凉。女主人叫张莲存,是从青海嫁到甘肃民勤这个村子的。
我们只是这个村借宿一夜的过客,但那个夜晚叫人难忘。后来看那位驻村干部的一篇驻村日记,写张莲存的丈夫放羊回家后喊他去喝酒,张莲存做青海的美食“山药疙瘩”,山药疙瘩蘸着蒜泥,再就着茴香茶,那叫一个好吃。吃饱了喝酒,张莲存性格爽快,也大杯地喝。几个人酒喝酣了,张莲存唱起青海的花儿:
大路上上来的荡羊娃
手拿了三尺的鞭杆
我把你心疼着擦一把汗
你给我漫上个少年
我看他写的这些文字,觉得那个星光下黄泥地上的小院更加生动了起来。与我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就在那个紧靠着沙漠的小村里,那样的欢乐似乎是成倍的。
二
唱歌的叫二毛,留个闪闪发亮的光头。
我们都有些微醺,请客的人赶在我们前面醉了。
是在哈巴河县一家农人的饭馆。
新疆哈巴河县,在中国地图大公鸡的尾巴尖儿上。同行的哈萨克族人说,哈巴河县境内有额尔齐斯河、哈巴河、别列孜河、阿拉克别克河,用哈萨克语说每条河时都带着唱歌的音调。
每条河的名字里都有好意思。
哈巴是一种叫五道黑的小鱼,因为河里盛产这鱼,河就叫哈巴河,地方就叫哈巴河县。在哈萨克语里,哈巴的另一个意思是“森林繁密”。白天,我们去了茂密的白桦林,就在落满云朵的额尔齐斯河的近旁。
坐在藏着岩画的多尕特洞穴的岩石上鸟瞰,天地辽远,一个个巨大的怪石像被神的大手摆放,远处有成片的庄稼地,这是神人同在的地方,近在身旁的还有多尕特岩洞的岩壁上一万多年前的马鹿、山羊、骆驼、狼、虎、开弓的猎人、日月星辰……金色的欧洲杨树林上,绸缎般的云彩慵懒地耷拉下一半。野生枸杞树,细密艳红的果实结实地簇拥成箭一般的枝条,刺向天空。广袤啊,鸟群从头顶飞过,哈萨克人在吟唱: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像对亲人诉衷肠。
桌上是哈巴河的鱼宴,大大小小各种鱼,还有一杯杯酒。窗外沉入邈远的黑色,沉静丰厚。弯月低垂。二毛沉浸在他的歌里。
……
爱人的毡房远了看不见了
一遍遍望你,看不见你
小鸟的脖子酸了,心里伤了
歌声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天的行走,我们一直恍若陌路,原来,一首短短的情歌就可以把我们一下子拉近。大家的面貌已经模糊,我们沉浸在几乎澄明的世界,正靠近一个叫灵魂的地方。或者还因为酒,这刚烈醇净又柔软的液体,拨开我们身上的雾障,让我们看见真的自己。
我还想起一次意外的出行,四个不熟悉的人,因为开会的机缘,一拍即合决定会后一起出游。那里是东海岸边,对我们四个人而言,陌生而新鲜。东西南北的四个人,带着四种长相、四种口音,坐渡轮,过外海,到一个小岛,或者快到傍晚时赶到一个仙境似的寺院,我们各自体会着远方的意义。吃饭时,我们看着彼此的面容,讲故事唱歌。故事的气味迥然,东西南北,那么奇妙。还有歌声,西北的藏人,心里辽远得厉害,歌声再小,歌儿也远得九曲回肠。
夏天的河涨了
过河的木桥淹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呀
我绕过源头去见你
一句素白的结尾戛然而止,一下子震荡了五脏六腑。
清澈辽阔的远方,把我们拥抱成一个婴儿。
那个东海边江南的夜晚,暗香浮动,一朵朵栀子花在夜色里开得明艳。
那是中国最西北的哈巴河县,白桦大睁着一树干有故事的眼睛,望着尘世。
天地苍茫,小鸟的脖子酸了,这样的诚挚,配那样广袤的自由。
三
有四百多年历史的黄土夯筑的卯来泉堡,像戈壁上残存的牙根。
车一直在戈壁的缓坡上颠簸爬行,戈壁一望无际。突然,天空下,这个破损的金黄色堡子映入了眼帘,心里一动。车继续爬坡。惊叫。绵延无边的祁连雪山出现在面前,就像一幅万千笔法皴染的巨画,立在卯来泉堡的对面。薄雪像一张毯子从卯来泉堡铺到雪山脚下。我从未这样近切地靠近雪山,太阳藏在厚厚的云里——这神性的自然,叫人震撼,却无从言说。
这景象始终难忘,我后来时常回想卯来泉堡,捕捉记忆中的点滴,回想那个显得不够真实的远方。我忆起第一次到那里时,凛冽的寒风刀子一样刮得脸疼。无法言说,嘴巴张开时,你发现话语都冻结在胸腔里。一群土色的沙鸡在欢快奔跳。堡子外面卯来泉泉眼四周,结着一层睫毛似的冰花。从堡子一直到祁连雪山之间,空中拉着薄薄的雪雾。后来偶然看到了谷歌地图上的卯来泉堡,上天的视角,堡子像戈壁上的一个微渺的院落,拉远了,只剩影子。它的北面正对着嘉峪关长城的最西头,它的南面也就是它的正面,是祁连雪山的一个豁口,历史上匈奴人、吐蕃人、蒙古人闯关的唯一通道。
卯来泉堡是一个守护神。
这一次,穿越三百多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路途中是一望无际的干燥的戈壁沙漠,还穿过了大雪纷飞的阴山。继续靠近卯来泉堡,我想,它已是我的一个坐标。
依旧被震撼,那个巨大肃穆的神——祁连山新雪覆盖旧雪。卯来泉堡又苍老了一岁。黄昏的太阳明亮地高挂,雪亮得耀眼。不同于前一次,一家牧人穿过祁连雪山,从夏牧场到冬牧场来了,雪山脚下这片平阔的戈壁上,羊群在雪里觅食,咩咩的声音混响出空灵的一片。
就这样,沧海一粟般落入这远古到当下的无边的时空,仿佛从家门口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俗世的思虑被抖落一空,就做一粒微渺之物,让戈壁上亘古不息的荒寒寂寥的风打磨和修正吧。
雪山真大,牧人说,这算不了什么,下了新雪的这些近前的山只能叫小山,真正的大雪山站在它们后面,只有进到雪山里面才能知道雪山真正的大。
牧人说,雪山里当然会遇见熊、狼,还有别的家伙,它们是雪山养的孩子。你只知道怕他,却没想到它们有多怕你。见着它们你只管静静躲开,千万不要和它们的眼神对上,只要对上眼神,它们的眼睛里会立刻烧出火苗子。牧人给我讲这些,我思忖着有一天也能穿过雪山。
坐在堡子脚下,等太阳落山。太阳落山是倏忽间的事情,似乎带着分量,一同落入那个未知世界的还有万千光束。一瞬间,四周的光景和气氛变了,万物要歇息了。
刊于《西部》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