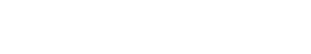作者简介
林素,本名易鹤,女,1993年生,河南信阳人,2020年博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现就职于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作《Mr·K》发表于《青年作家》。
Mr.K2
林素
在遇上K先生之前,我的生活受控于另一位。我曾一度以为,他和 K 先生是一分为二 的,甚至可以这样讲,他们明明就是一个人,如果我愿意称之为人的话。现在想起他,最深的记忆源自一次重逢。那是一个雨夜即将消失的时刻,潮湿的空气一点点地往屋子里钻,微冷的风在窗台上噗噗地打着照面。与之形成 强烈冲突的是另一种干燥的声音,我仿佛能够想象什么东西的爪子一遍又一遍地扒拉着木门,离我那样近,以至于耳膜开始颤抖。
他终于带着死灭的气息闯进来,仿佛君主降临他的领地,我不敢动,也不能,甚至无法睁开眼睛看一看。当死亡离我很远时,我急切地 寻找它,但到了危险时刻,我又无比渴望活下 去。意外的是,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一种巨大而有形的悲伤开始在我们之间弥漫, 像紫色的烟填满了这个空旷的房间,那是我不 能理解也从未遭遇过的情绪。他没有开口,我也没有勇气问询。就这样,我们被时光遗忘在那个画面里,虽然一个拼命祈祷逃脱,而另一 个丝毫不为所动。黎明的降临结束了这一切, 我从没有这样喜爱过它,却再也无法释怀。
我努力回忆关于这位的一切,许多年,却没什么印象。抛却对死亡的恐惧后,他成为我和另一个世界的连接点。偷偷地打开一个缝 隙,让他倾泻出一些悲伤而隽永的情绪来,在不能承受之前,又偷偷地关上。而K先生的到来慢慢解开了记忆里所有带锁的东西,我终于记起了他是谁,呵呵,多么讽刺,我亲爱的“哥 哥”。虽然我总是怀疑他们的同一性,但每当这样的念头升起,我又总能找出新的一点不同来。他的样子柔和庄重,而K先生精致凌厉,他的行动大开大合,而K先生谨言慎行,最要紧的是,他身上丝毫没有K先生人性善良的部分,他是冰冷的、神性的、复杂的,我从来看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无论如何,他是另一位 天才,在我不长不短的童年记忆里,刻骨铭心地存在。
他本该如我一样出生,但或许是哪里出了岔子,我们只好共用一个身体。说是共用,事实上,是他搞丢了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被共用的身体说到底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只是有时大大方方地借给他,在他需要的时候。讲这样的话难免要唾弃一下自己,如果此刻他还在的话,我应该会再次听到那个讽刺而尖锐的声 音。我对他的厌恶和依赖都是基于他是天才而我不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数年来我都试图改变这一点,但我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自从他走了以后,我变得普通了许多。
我也时常想,难道我们真的是两个人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平庸和懒惰归结于他的出 走呢?为什么要把年少时候做的那些错事都推脱到这样一位天才少年的身上?或许是我无法相信那个每天下午都要蹲在楼下踩蚂蚁的人是我,那个和同学打架的时候下死手的人是我,那个小心翼翼讨好父母老师的人是我, 那个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的也是我。但这又能怎么样呢,我已和他划清界限,也就意味着我不再承认这些事和当下的关联,连我自己都觉得讽刺,何况他呢。他走了之后,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无法对自己的性别有确切的认知。那些真真假假的暗示和接触,无论男女,除了长发时的K先生,都让我觉得恶心。
奇怪的是,我总是梦到类似孕育的东西, 随之而来的是死亡。我一个人走在空荡的大 街上,目的地当然是医院,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一种形状,它会成为人吗,还是只是一种疾病?我被装进抽真空的袋子里, 空气一点点地离开,这样一种古怪的形状也离开,而我失去了对这具身体的使用权。我还是很想活着的,虽然要和这样一个怪东西共处。它从哪里来的呢?它真的是婴儿么?“当然啦, 不信你摸摸看,在动的”,医生这样和我说,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巨大的骗局。每一次都是 以我的死亡告终,我总觉得它预示着什么。我想起一个玩笑,那时我很不情愿再和他共用身体,出了一个离谱的怪主意:“要不你做我儿子好啦,你这样聪明,我一想到以后如果要生一 个蠢货,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他好像感受到了这个主意的诱惑力,挣扎了一下还是拒绝了。
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玩笑直接导致了他的离开,可能他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我的某种不情愿。我说不上来当时的情绪是失落还是欢欣,因为终于我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了,而我们也走到了十几年来第一次告别的时刻。“还会再见么?我要去哪里找你?”我带着一丝 希望问他,却在他脸上发现了一个勉为其难的笑容。“我会回来的,但你不要等我。”他走得悄无声息,而我也从一个要靠吃药维持生命的病秧子,变得和普通人相差无几,至少看起来是差不离的。我生平第一次有了清醒的感受,我激动得想要大哭,发誓不再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操控我的意识,绝对不行。没有经历过这一 切的人是永远无法想象的,不是我对数十年来的感情视若无睹,而是如果霍金恢复了对身体 的控制,那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说服他回到轮椅上的。我对他的想念也是真切的,我幻想着他找到自己的身体回到我的生活里,那时候他还是我的好哥哥,我也愿意继续和他相依为命。
从小到大,我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他很少在白天开口说话,除非是有什么非要立刻告诉我的事情。比如说,学分数的时候,他让我不要听小学老师在那里瞎掰扯了,他要给我讲讲极限。这是很新奇的,对一个小学生来 说,1/2,2/3,3/4,4/5,5/6,可然后呢,永远呢,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本质。后来,关于这件事情他又给我讲了一次。在大学的课堂上,他要我注意约当测度和勒贝格测度的区别。“无穷大?”我不大理解他的意思,但他不再回答我了,我只好拿着书去问老师。我对这个举动是有些后悔的,因为老师认为只有一个读完了整本书又很有天分的人才能问出这样核心的问题,而他还大声地在一个上百人的课堂上说了出来。这最终也促使我为了维持大家的某种 错觉而不得不格外努力些。
天地良心,我对他的依赖不在于考试或者什么时候他会把正确答案(尤其是选择题的答 案)告诉我,而是某种程度上他像守护者一样 时刻准备要救我的命。我被车撞过,从楼梯上 滚下去过,每次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身上也只是擦破一点皮而已。我当然知道这是他的缘故,更要紧的是,如果我真的死掉了,他还可以顺其自然地接管我的身体,从此替代我, 但他好像并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有时候我 甚至诡异地想,会不会我在某一次事故中已经死掉了,而现在的我其实是当年的他,由于不肯承认这一点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记忆。
当然这也只是想想,毕竟他是天才中的天才,我却是拼尽全力的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 还要糟糕些。我的记忆有些老年痴呆的征兆,甚至记不得自己午餐吃了什么,有时候也会在 自己家附近迷路,尤其是晚上。那天我骑着单 车跑远了,忘记怎么回去,当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像看到了救世主一样,感动得语无伦次。如果所有发生在我俩之间的事被 第三个人看到,他一定惊讶于世间还有这样的疯子。我蹲在车子旁边呜呜地哭,他小声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回去。”
他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说,只是对我这个唯一的妹妹心慈手软,安慰人的方式也带着某种恶趣味。我和父母相处得时好时坏,有时候气急了还会爬上阳台的护栏想往下跳。他是怎么和我说的呢?他说:“你看看,咱家在四楼,也就这么高点儿吧,我估摸着你跳下去也死不掉的,但摔残废倒是没啥问题,你想清楚了就跳吧,不过我还是建议你选个确保 能死透的方式,到时候我就用你的身体继续和 爸妈好好处,没准儿还比你更讨喜些。”我气笑了,哼,偏不要便宜你们父慈子孝。他也不说 话,只是笑笑,一脸玩味地看着我。
我对他的不善良一直是听之任之的,还带有一些赞赏,但分歧发生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那天我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春天的花和漂亮的小女孩,多么和谐的景象。我有些累了, 蹲坐在地上看她扑蝴蝶。她一直没有捉到,有些着急,甚至激起了胜负欲。最后,小家伙还是落到她手上。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只 是一瞬间,猝不及防,她把那只小白蝴蝶撕碎 了,就像撕一张纸一样,碎成一片一片的。她笑得很开心,像春天的花,我却好像受了某种 严重的刺激,当天就病了。我迷迷糊糊地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蝴蝶,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激起一阵恐惧和恶心。从那以后,我见到蝴蝶都躲着走,有些不识趣的还老爱往身上扑, 吓得我四处逃窜。奇怪的是,那个女孩后来遇 到了好些倒霉事,她的命运就此改变。我试探 着问了下哥哥,他没有否认,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说:“你没有权利改变别人的命运。”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严肃,也答应不再这样做了。我从此对他的胆大妄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担忧也多了一些。
他离开之后,我的快乐并没有持续非常久,因为我发现,不再有人把我看得那样重要了,我对这个世界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转变,越来越难以和自己相 处。我会在冬天的晚上搬着凳子到阳台上看 月亮,丝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这样的举止。我买了很多白酒,睡前倒在茶杯里,一口气喝 掉,昏昏沉沉地往上铺爬。我不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失眠,还是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我在自己的梦里死了又死,鲜血滚烫的温度多么让人着迷。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倒是时常梦到 K先生,冷漠的K先生,温柔的K先生,才华横溢的K先生,时刻挂念我的K先生。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也看了许多风景,度过了各种各样 的快乐日子,却始终没有走出理想与现实的边 界。他会是哥哥么?他会记得我吗?为什么我们之间仿佛是爱情呢?这是合乎伦理的吗?
初见K先生的时候,我在他身上发现一种熟悉感,就像是一个陶土做的人偶,发现了同 一把土做出的另一个。我听着那种召唤灵魂的声响,感觉无比惊奇。或许我们来自另一个星球,这可以略微解释我们与这个星球格格不入的部分。与我的平庸不同,他似乎有一种入侵般的来势汹汹。我从未见过如此惊心绝艳 的人物,也很少有机会如此切身地感受人生的起伏。不管是出于对同类的保护,还是对天才的向往,我都对他有些特别的责任心。当我发现他的心情如同我站上自家阳台时,格外不忍心看他张开的手臂。不可以,无论如何我不能在这时沉默,我应该要讲点什么。耳边回荡着 那个略带讽刺的声音:“你如果死在这儿,他们就高兴了。”我语无伦次地讲:“还有很多事要做不是吗,你注定要去承受更多。”终究他还是走过了那个阶段。生命是不能假设的,我有些庆幸和后怕。
全文请阅读《西部》2022年第2期